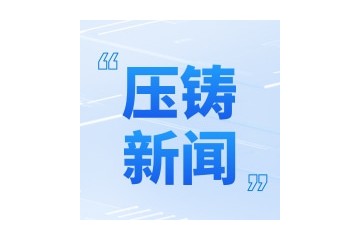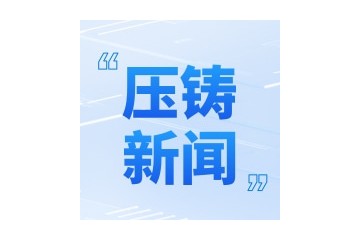“碧礦不出土,青山鑿不休;青山鑿不休,坐令鬼神愁。”這是梅堯臣對古代銅陵人民開采銅礦石艱辛的摹寫。

如今,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全面落到實處,做到資源循環利用,產業轉型升級,銅陵有色正走在高質量發展新路上。
資源“吃干榨盡”
“目前,我們對資源已經做到了吃干榨盡,實現了高效利用。”銅冠冶化分公司紀委書記、工會主席謝權自豪地說。
一直以來,銅陵有色堅持走綠色開采、保護生態的礦山建設新思路,努力以最小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獲取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對新建礦山,采用新模式和現代化開采技術,使金屬回收率和資源利用率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冬瓜山銅礦是采用國際先進技術建設起來的礦山,基本做到“廢石不出坑、尾礦少入庫”,已成為中國深井礦山開采的標桿。礦山從設計到投產大量采用當今世界先進技術與工藝,以國際一流的工藝裝備、亞洲一流的規模效益,國內一流的管理體制,建設成為現代化生態礦山。
然而,多年開采,冬瓜山銅礦產出的大量硫精砂處理成為一大難題。市場行情不好,硫精砂長期堆放不僅占用土地資源而且還會自燃,污染環境。為此,銅陵有色以年產80萬噸硫酸、年產120萬噸鐵球團、年產4萬噸碳酸二甲酯等項目為依托建起了循環經濟工業園。
在園區,銅冠冶化分公司經理助理李要武介紹說:“這些項目利用冬瓜山銅礦生產的硫精砂,作為硫酸項目焙燒制酸的原料;利用制酸生產以后的硫酸燒渣,作為鐵球團生產的原料。同時回收硫精砂焙燒制酸過程中,硫精砂自身所產生的大量的熱能進行余熱發電,再利用余熱發電以后的蒸汽作為生產碳酸二甲酯的能源,基本上做到了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
產業綠色發展
“我們使用的閃速熔煉爐、閃速吹煉爐是密閉爐,煙氣濃度很高,煙氣量小,主煙氣通過凈化、除霧、干燥、轉化后用來制造副產品濃硫酸,制酸后尾氣經脫硫系統處理后排放。”金冠銅業分公司總工程師張志國指著生產工藝流程說,放銅、放渣口溢散煙氣通過收集形成環境集煙氣,公司投建環集煙氣脫硫系統,保證尾氣達標排放。
金冠銅業分公司擁有當今中國銅工業先進的綠色銅冶煉技術,采用先進的閃速熔煉、閃速吹煉、永 久不銹鋼陰極法電解、動力波洗滌兩轉兩吸制酸等先進工藝,硫總捕集率達99.97%,水循環利用率達97%以上,資源可完全實現內部循環利用,已成為世界銅冶煉的樣板工廠。
“加強生態建設,推動綠色發展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銅陵有色的聲音鏗鏘有力。2017年4月20日12時48分,隨著zui后一爐銅吹煉結束,標志著有45年歷史的金昌冶煉廠生產系統全面關停。在舊廠退出歷史舞臺的同時,一個更加環保、高效的銅冶煉“奧爐”項目已拔地而起。項目建成后,將促進銅陵有色形成完整的高、中、低品位含銅物料處理系統。
市民李新慧說:“以前,我們在市區有時還能聞到一點硫磺煙的味道,你看,現在空氣多好,經常是藍天白云。”
據了解,銅陵有色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如今呈逐年下降趨勢,約占銅陵市二氧化硫總排放量的十分之一,而創造的工業總產值卻占銅陵市一半以上。
補短板延伸銅
長期以來,銅陵有色在銅開采、銅冶煉工藝水平上一直執國內行業的“牛耳”。
但銅深加工卻仍是“短板”,許多銅加工產品還只是常規類型。如何更好地推動銅產業轉型升級、邁向中高端?銅陵有色立足高起點,按照“高檔次、差異化、大規模”的思路,延伸銅材精深加工產業,以存量升級和增量轉型,為企業發展不斷注入“綠色基因”。通過開發和生產技術含量高、適銷對路的銅及銅合金精深加工產品,拉長銅產業鏈,先后建成高精度銅板帶、特種漆包線、磷銅材料、電子銅箔、高導銅材等項目。
幾年前的銅桿產品,還是銅產業鏈上的一個短板。為了補上這塊短板,銅陵有色借助省市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支持,加大技術創新力度,高標準上馬了年產量22.5萬噸低氧銅桿的高端銅線材加工項目。“我們公司建廠之初就走高端路線,引進國際先進的連鑄連軋生產線,生產出的低氧光亮銅桿,不僅填補了銅陵有色產品鏈條上的空白,也改變了省內銅桿產品主要從省外采購的局面。”銅冠銅材公司副經理方勇此言不虛。這個公司生產的高導銅材是安徽省戰略性新興產業——銅基新材料產業核心產品之一,具有含氧量低、導電率高、延伸率好等特點,廣泛應用于核電、高速鐵路、海底電纜、汽車、通訊、電磁線等行業。2017年倫敦金屬期貨交易所正式向這個公司頒發了注冊銅測試工廠資格證書,打開了通往國際市場的綠色通道。
2017年,銅冠銅箔公司已建成合肥、池州、銅陵3個銅箔生產基地,成功邁入行業第 一方陣。2018年上半年生產銷售銅箔10128噸,產值7.2億元,利潤1.08億元,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把集團公司打造成盈利能力良好、產業優勢突出、創新能力明顯、人企共同發展的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國際化企業集團。”銅陵有色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楊軍的話語擲地有聲。在新一輪高質量發展大潮中,銅陵有色已由各產業內的小循環逐步發展到跨產業的大循環,從單一產品的循環到園區的集成循環,建立了動態的立體循環經濟體系。
 客服熱線:
客服熱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