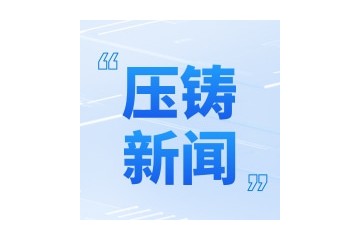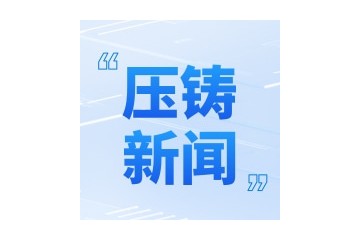按照道家無為而治的觀點,管理的理想境界是看不見管理,而按照佛家的邏輯,則應該叫做“非管理”,其實質(zhì)是每個員工在每個環(huán)節(jié)都進入自我管理的狀態(tài)。
“非管理”是按照佛家的邏輯推導出來的概念。佛家在闡述佛詣時經(jīng)常使用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方式。例如:“所言一切法者既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金剛經(jīng)》第十七)這樣的例子很多:“莊嚴佛土者,既非莊嚴,是名莊嚴”;“佛說般若波羅密,既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若波羅密”;“如來說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將這樣的程序用形式化的語言表達出來,則是:
X,
非X,
是名X。
把企業(yè)管理的概念代入,就可以推斷出:總經(jīng)理者,既非總經(jīng)理,是名總經(jīng)理。同樣的:管理者,既非管理,是名管理。這就是“非管理”的由來。
管理與非管理的關系,不是有與無、是與非,而是名與實的關系。既然管理是名,那么非管理則應該為實。如果沒有非管理的存在,管理就徒具其名;而管理之名必須通過非管理的實現(xiàn)才有意義。非管理并非是對管理的排斥,而是對管理的揚棄和升華,可以使管理得到更好的落實。非管理并不是管理范疇之外的東西,也不是做與管理不相干的事情,而是一種自覺自為的管理。比如在美國聯(lián)邦快遞公司的工作現(xiàn)場,看不到管理者發(fā)號施令,每個人都在積極主動的履行自己的職責,“自己管理自己”成為員工的生存之道。我國的海爾集團實行“流程再造”,通過內(nèi)部“壓力傳導機制”使得員工在自我管理中充分釋放出自己的潛能和優(yōu)勢。這都屬于“非管理”的狀態(tài)。正是因為有這種“非管理”在發(fā)揮作用,原來的管理便成了名義上的管理。
一般認為佛家以普度眾生為己任,佛主卻予以否認:“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度眾生。”“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相。”(《金剛經(jīng)》第二十五)那意思是說,假如佛主如來作出了這種承諾,只會迎合凡夫的俗念,也把自己與凡夫俗子混同了起來。普度眾生的任務只能通過眾生自己度自己來實現(xiàn),這給企業(yè)管理的啟示就是,管理的任務只能通過被管理者自己管理自己來完成,既然不可能實施一對一的管理,也不可能指望一對多的管理能夠奏效。相比之下,佛主要比那些自稱包治企業(yè)百病的管理大師更具有自知之明。
媒體常有企業(yè)家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的報道,如果他們能夠及早悟出非管理的道理,也許不至于那樣透支自己的健康。可以設想,管理者以管理別人為己任,等于將自己置于眾多被管理者的對立面,當然活的很累。實際上,在管理博弈中,離開了管理權的強勢,管理者并不比被管理者高明多少;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輪番過招中,雙方誰都得不到“超度”。反過來說,管理者如果能夠引導和發(fā)動管理對象自己管理自己,通過非管理獲得管理的靈氣,就可以變與管理對象的博弈變?yōu)楹献鳌U缣拼赫髟凇吨G太宗十思疏》中所說:“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官之役哉。”
當然,追求非管理不是放松或者放棄管理,而是對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個員工在每個環(huán)節(jié)都能進入自我管理的狀態(tài),靠的是機制,靠的是文化。在管理機制和企業(yè)文化的建設中,管理者的無為其實是更加有為,是更大的有為
 客服熱線:
客服熱線: